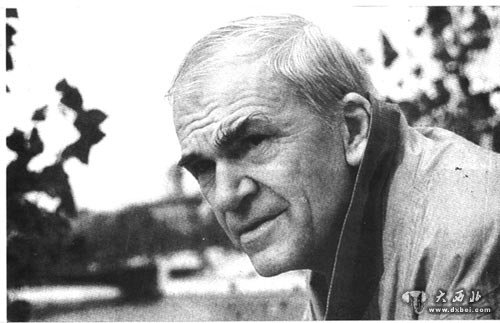
在我的阅读视野中,昆德拉一向都是那种很聪明的作家,这种聪明不仅表现在小说创作中四两拨千斤化重若轻的写作手法,更表现在对现实和政治形势审时度势的态度上。
1968年,前苏联入侵捷克不久,昆德拉刚发行不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玩笑》被禁,随后也失去了电影学院的教学工作,他立刻意识到在捷克以后的生活和写作都可能无法为继,于是干脆选择流亡,远去法国定居。事实上,在面对极权统治和审查制度时,我们有权选择离开或留下,这两种态度都无可非议。昆德拉选择离开,还有很多作家选择了留下。但是对于昆德拉来说,他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地面对这种生活状态吗?
某种程度上,昆德拉在法国一直经受着一种内心的煎熬,他能够通过创作去控诉和揭露捷克被前苏联侵略占领的真相,用这种方式化解他内心无法与他的同胞和同事同甘共苦的负罪感,但是内心的原罪还是无法消失。国内批评家对昆德拉十分憎恶,因为当昆德拉获得最高世界声誉的时候,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正处于和极权体系作艰苦斗争之中。当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流亡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协同作战,经历各种各样的艰辛时,昆德拉却远在巴黎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。
我们现在读到昆德拉的作品中有法语,也有捷克语的作品,换句话说,昆德拉在写作的时候选用了两种语言,姑且不论孰优孰劣,但是其中彰显出的还是一种聪明现实的文学策略,双语写作,面向不同的读者和大众。但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,昆德拉在《相遇》中提到了一个讽刺的例子,大作家纪德编选诗选,没有收录米沃什的作品,因为觉得米沃什的诗歌不值一提。这点惹恼了昆德拉,他颇有讽刺意味地说,米沃什的诗确实不属于法国,他保留了波兰语的根基,“逃到法文里,宛如躲入僻静的修道院里。就让我们把纪德的拒绝当成某种高贵的做法,为的是保护一个异乡人不容侵犯的孤独:一个永远的异乡人”.
“一个永远的异乡人。”昆德拉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自己。这是昆德拉的尴尬,一个流亡者的尴尬,他已不是捷克作家,也不会是法国作家,他只能生活在别处。










